事实上,杨月华已经从梦里挣脱出来,只是她不敢确定。
她伸手往身边一摸,这是她几乎每次醒来都要做的动作。白菜缩了缩身子,呜地叫了一声。她嘘了口气,把手缩回来,抹了把额头上的汗,梦里那颗悬在天上的心终于落回了原处。
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屋子深处的阴影开始向着光亮处流动,黑夜和白天正在忙着交接。
外面下着雨,雨点滴滴答答地敲打着瓦檐。
对面的早餐店正在开卷闸门,哗啦一声之后,似乎是卡在半腰间了,开门的人拿了样什么东西使劲地砸着门,像在发泄着内心的仇恨。随着门的晃动,砰砰的声音如波浪般冲击着小巷里的宁静。
砸门声停止后,陆续有脚步声从河那边传来,暗沉沉的,越来越明亮,最后终止在窗外的雨声中。
杨月华把白菜搂进怀里,白菜拱了拱身子,伸出爪子在她手臂上挠了几下,像在安慰她,又像在抗议她力用大了。她把手松开,又一次闭上了眼睛,想把梦里的事情甩得一根毛都不剩,再好好睡上一觉。几经努力,睡意还是没有听从她的指令,刚一上来就抱头鼠窜,像一朵待放的花背叛了春风招展的枝条。
这也难怪,她已经睡得够多了。从那里回来后,她似乎没做过什么事情,除了吃饭,就是睡觉,用这两件不算事情的事情打发着机械的日子。只有在熟睡的时候,她觉得生活是宁静的,天空那么高远,那么明亮,撒满了牛羊一样的云彩,和过去没有两样。而这种宁静,总是被接二连三的梦打破。她怀念以前的日子,一夜无梦,睡到太阳晒到屁股上还不想起来。现在,梦缠上了她,像狗一样撵着她团团转,她不时从噩梦里醒来,浑身抽搐,一头大汗,她深恶痛绝,又无可奈何。
她也想过去看下医生,很快又否决了这个愚蠢的念头。能治她病的,只有自己。现在,她也搞不清楚,要把自己治愈,需要多少个疗程。或者,再也没有痊愈的那一天了。
她翻了下身子,在想今天该做些什么,这是她想得最多的问题,每天一睁开眼就想,似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。别人都叹息时间不够用,她像个奢侈的女人,拥有花不完的时间,她只想找到一个办法,把这些过剩的时间挥霍一空。
冬天,白昼很短,对她而言,像枯竭的河流一样荒凉而漫长。想来想去,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她可以做的。昨天吃完早餐后,她把冰箱里的小豌豆拿出来,心不在焉地剥了,一粒粒豌豆躺在白瓷碗里,圆滚滚的,闪着绿色的光,这感觉,就像有很多双婴儿的眼睛在望着她。她突然觉得应该数一下到底有多少粒,她自己也吓了一跳,怎么突然会冒出一个这样古怪的念头。
她从壁橱里拿来一个瓷碗,放在椅子边,开始数豌豆。她弯下腰捻一粒放在左手心里,接着去捻另一粒。豌豆在她的手心里骨碌碌地滚动,弄得她痒痒的,她觉得这是一件充满意义的事情。等到手心里装不下了,她便一次性放进椅子边的瓷碗里。豌豆像调皮的娃娃,沿着碗边洁白的斜坡往下滚,在碗底蹦了几下,然后不动了。她慢吞吞地做着这件事情,直到第一个装豌豆的碗变得空荡荡的,她得到了一个满意的数字。
“和我猜的差不多。”她咕哝了一句。
她搓了下冰凉的双手,突然又觉得不对,好像不是这个数字,她决定再数一遍。
按照原来的方式再数了一遍,没错,还是那个数字。
望着碗里的豌豆,她一下子兴味索然,觉得这是一件极其无聊的事情,简直无法原谅刚才的自己。她抬起脚,想一脚踢飞那个盛豌豆的瓷碗,让它在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很快,她又把脚收了回来,踢飞了又怎CHUANGZUO 《屋檐下的天空》 小说矩阵么样呢?
她陷入了一种深重的沮丧,像是几百年前裹在松脂里那条无路可逃的虫子。她掀开被子,匆匆套上睡衣。她穿睡衣的日子多,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,几乎不用出门,她所谓的出门就是去菜市场。菜市场离家近,几乎可以望见,出门沿着巷子往右走,经过一些卖香烛纸钱的门面,还有两家卖宣纸和毛笔的店子,就到了五彩光幼儿园,过了幼儿园是教堂,从教堂侧边穿过开阳路就到了。
她经常穿睡衣去,再戴上口罩,买过菜匆匆赶回来。
杨月华往后拢了拢越掉越少的头发,把窗帘拉开一条缝,看到了屋檐下那线压得低低的天空,沉闷,粗糙,像一张刚剥下来的兽皮。雨还在下着,细细密密的,门口那条小巷里布满了水洼,暗黑色的光从水洼里泛了起来,像古董店里的老银子。对面早餐店里有几个人在吃早餐,门口停着一台红色的摩托,上面盖了件灰色的雨衣,雨衣上堆积着巨大的水珠,似乎有好几个人在同时朝她翻着白眼。
她把窗帘拉上,从冰箱里拿了个馒头放在不锈钢的盆子里,把盆子放进炉子里,再把炉子放在电磁炉上。按下按钮后,电磁炉发出嗞嗞的响声。她并不饿,吃不吃都无所谓,只是觉得早餐不能省,这是一种形式,假若把早餐省了,日子就更不像日子了。
馒头在冰箱里放久了,硬邦邦的,有些硌牙,啃了一半,她一把丢进了垃圾桶。
她把自己丢在那条虎皮色的布沙发上,弓着身子,双手撑在膝盖上,她习惯以这样的姿势安放自己。她懒得开火炉子,这大冬天,烤不烤火都是冰冷的。像水色一样难以描述的光线从窗户里进来,把她的影子抛在脚下灰白的瓷砖上,那一团薄如蝉翼的灰黑,佝偻,颓丧,像她的命运。她如同一个符号,就这样埋伏在自己的命运里。
回到这个家以后,她接受了这种命运的安排。
窗户下有几盆花,一字形排开,种在最廉价的赭色塑料盆里。这些都是她买菜时从一个卖花的中年女人手里半买半送弄回来的。有次她买菜时看到女人的推车上有盆茉莉,有几根枝丫耷拉下来,叶子枯黄,掉了不少,恐怕活不了几天了,只剩下其中的一根还在孤独地奋斗。她问多少钱,女人在确认了是那一盆后,用古怪的神情瞪了她一眼,随后昂起头,一副慷慨大度的样子,吐出两个字:“随便。”她给了五块钱搬了回来。后来,她每次都找那些品相差的花买,花个三五块钱便可买一盆。女人粗手粗脚地把花装进塑料袋里递给她时,总不忘用眼神对她进行一次拷问。
她总是躲开女人的目光,一手搂着白菜,一手提着花,像做贼一样急匆匆地往回走。她害怕和别人对视。
杨月华望了下那些花,想把它们搬到楼上去,至于为什么要搬到楼上去,她并不清楚。她住的是二层的房子,一楼是青砖砌的,二楼是木头搭的,木板黑漆漆的,像永远处在幽深的夜色之中。她和家里人都住一楼,二楼空置在那里,老鼠和蟑螂相继在这里安下家来,它们像人一样,添砖加瓦,储备粮食,生儿育女,把这里开辟成了快乐自由的天堂。
巷子两侧都是这样的房子,平时路过,到处传来吱吱呀呀的响声,像恐怖片中刻意营造的氛围,惊悚而神秘。她疑心哪一天,这些房子会在一场暴风雨中分崩离析,砖头、木板、钉子、檩条被风抛向高空,然后在风雨的怂恿下,各自尖叫着,纷纷扬扬奔向通往废墟的归途。
周围都建起了崭新的小区,高高的楼群,矗立在欢乐的草坪和花草树木之间,仿佛属于另一座城市,一刻不停地招来整条小巷的嫉妒和怀恨。这里也多次说过要拆迁的,因为附近的那个老教堂,地产商不愿去动上帝的奶酪,更重要的是担心房子卖不出去,都不愿买这块地皮。就这样在眼巴巴的期盼里,一年年拖着,最终沦为了县城里的贫民窟。
她搬着一盆栀子花往楼上走,布拖鞋踩在木楼梯上,跟白菜的爪子落在上面一样,无声无息。这些年,她跟白菜相依为命,习惯了白菜的跟随,她到哪,白菜就跟到哪,睡觉时,她把白菜放在身边。早上醒来,她都要伸手摸一摸,一旦没有摸到白菜,她就会吓得从床上蹦起来。
白菜是一条流浪狗。她回来后没两天,有天早上打开门,一条脏兮兮的小狗从大雾里扑了进来,呜呜地叫着,围着她转圈,咬她的裤脚,最后,抬起头,用茫然而感伤的眼神望着她。她心里一动,眼泪落了下来,打来水给它洗澡,热了馒头喂它,洗过澡的小狗一身白毛,蓬松,柔软,目光清澈,她再次感到一条狗比一个人更值得信赖,她把它留了下来,随口叫它白菜。她觉得这是上天的成全,上天亏欠了她,打发白菜来弥补她人生的裂缝。
等她把最后一盆波斯菊搬到楼上后,电话响了。她想不出是谁打来的。平时,很少有人给她打电话,她手机的通讯录里不超过十个电话号码,除了李典平和谭红以外,都是家里人的,陌生的电话打进来,她看一眼就会毫不犹豫地按掉。
杨月华拿起手机,电话是儿子打来的。
“妈,我放假了。”
杨月华愣了一下,才回过神来,意识到寒假到了。
“哦,就放假了吗?”她心里不是这样想的,可是话一出口,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儿子上大三了,和姐姐一样,对母亲总是百依百顺,不管她怎样,从不跟她计较。
“妈,给我做点好吃的。”儿子嘻嘻笑着,在电话里撒娇。
“嗯,知道了。”挂了电话,她恨不得在自己腿上死死地掐几下。她问自己,为什么要挂这么快,就不能多说几句吗?
杨月华下了楼,戴上口罩,抱着白菜匆匆赶往菜市场。
一路上,她都在想儿子喜欢吃什么。她在脑子里转了几圈,想到了炖牛排、红烧猪蹄、剁椒鱼头,她确认是这几样。
买了菜往回走,经过五彩光幼儿园门口时,听到里面传来风琴声和孩子稚嫩的歌声,大概是在举行这个学期最后一次活动。
她想起儿子小的时候,她从麻纺厂下班后去接他回家,她牵着儿子的手,儿子像只兔子一样,在她身边蹦来蹦去。天空看不到边,像一湖蓝墨水,满怀清澈的深情,夕阳把门前的巷子染成胭脂的颜色,她的身体里像有一条河流,哗啦啦地流淌,她听到浪花飞起来,叮叮当当地溅开,然后,像雨点一样沙沙地落下,变成一朵朵桃花,一盏盏灿烂的星光。
现在,桃花凋谢了,化作了污浊的泥土,星光埋在了乌云的背后。
要不是下岗后去南方打工,在那个嘈杂的车站,喝下了那个慈眉善目的女人递过来的一杯该死的饮料。
唉—一切都无法挽回了。
她擦了下眼睛,加快了脚步。
牛排焯了水,放在炉子里炖,水不停地翻滚,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,热气腾腾地冒了出来,围着她游动。鱼头腌在盆子里,蒜泥、紫苏、剁椒均匀地撒在上面,像铺着层秋天的阳光。猪蹄已经洗干净,接下来得准备蒜苗、茴香、八角,还得放一两枚草果,切一把大红椒。杨月华在厨房里忙碌着,暂时的温暖在她的内心荡漾。
估摸着儿子快到了,从省城到家,也就一个多小时。杨月华站在窗前探着头往外望,雨停了,巷子里湿漉漉的,偶尔有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过。
杨月华望了四次之后,儿子回来了。他进门后把那个棕色格子的拉杆箱往门角一推,箱子顺从地靠在墙壁上,不动了。他像小时候一样,一把抱住杨月华,一脸笑嘻嘻的。“妈,我回来了。”
杨月华本能地一把推开。“好,回来了好,我去给你做饭。”
她转身往厨房走,白菜一路小跑跟着她,白色的毛一荡一荡的。
儿子又长高了,她多想给儿子一个拥抱,摸摸他的脸和头发,和他说上一会儿话。可是—
她想起青梦,她嫁给他后,就一直这样称呼他,她喜欢这个称呼。一个梦字,显得亲昵,又概括了这个男人身上的特点,五大三粗的身架,透着种傻傻的憨厚,成天乐呵呵的,像个没长大的孩子。那时候,他在一家农业机械厂上班,县城里的人称为“农械厂”。厂子在东方路,那是一条只有几百米的横街,大门正对着街道,几栋摇摇欲坠的房子,就是车间,地上铺着层铁屑,铁屑上乱七八糟地躺着切断的钢管,长了锈的齿轮和钳子。机器转动时,发出震天的轰鸣,说话得大声吼,不吼就听不见。灰尘一刻不停地飞舞,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青梦是车工,那是个累活,还是个危险活,一不留神,一个脚掌、几根手指就有可能被不讲情面的钢铁吞掉。他回家时很少说厂里的事,总是笑眯眯的,还经常在兜里揣一些小东西,那些东西五花八门,有吃的也有用的。有时候他下班刚踏进门,她就会扑上去掏他的布兜。他举起双手,呵呵笑着,任由她的手在里面捣鼓,很快便在其中一个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来,有时是一把小梳子,一条丝巾,一个发夹,有时是一袋干果,或者一小盒刚上市的樱桃。有一次她居然掏出两张电影票,她惊喜得像个捉住了一只蜻蜓的小姑娘,拿在手里左看右看,没想到向来大大咧咧的他也会想到陪她去看电影。
有时候她故意不去掏,装作没那回事,目光却追随着他的一举一动,看看他会怎么做。他先是反复在她面前踱来踱去,引诱她伸手,见好一阵没有动静,才走到她身边,把手伸进兜里。“看,这是什么?”他握着拳头伸到她面前。她伸手去掰他握紧的拳头,他死死攥着,等她不用力了,他突然猛地松开,嘿嘿地笑。“没有。”她佯装生气,把脸扭过去。他很快把她意想不到的一样东西塞进她手里。
她回来的那天,青梦上班还没回来。屋子里的一切都变得陌生,窗户敞开,地上乱七八糟地丢着脏衣服和袜子,怪味浓得可以堆积起来,像她脸上化不开的哀愁。墙上的霉点越发浓稠了,好像松开了捆绑,即将挣脱墙壁的禁锢,加入到这个家庭中,成为家中的一员。老家具似乎刚从一场古老的梦中醒来,用惺忪的睡眼,打量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女人。
晚上,她缩成一团,隔青梦远远地躺着。她一直都没有睡着,觉得屋子里的柜子、床、墙壁和天花板都在向她逼近,睁着眼睛在监视她,偷窥她,跟踪她。半夜时分,青梦伸出手来抱她,手触到她的那一刹那,她像发了疯一样对着他的脸使劲抓挠,他猝不及防,脸上被抓出一道道血痕。她爬起来,站在床前,低着头,揩着脸上的血,像个犯了错的孩子。
他从壁柜里拿了床毯子,睡到了沙发上,后来他就一直睡在沙发上。杨月华清醒过来后,呜呜地哭了,她决定离开这个男人,命运不负责任地推了她一把,让她莫名其妙地成了这个男人的“敌人”。
只有离开,才是最好的结局。
青梦活着,只活在过去,已经死在了她的心里。她没有了过去,她的过去已连根拔起,埋在了时间深处。现在,就连对青梦的称呼也变了,她再也喊不出青梦这两个字,在别人面前,她称青梦为“他”,在他面前,她称青梦为“你”。
她收拾了几件衣服,准备趁着夜色离开这个家。出发前,她去房间里看女儿和儿子,跟他们默默地道个别。那会儿女儿上大一,儿子上高中。她看到他俩睡得很沉,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特别是儿子,眉角有一丝隐隐约约的笑容,大概在梦中正走在一条通往幸福的路上。她那颗母亲的心顿时化成了水,转身回到房间,把收拾好的东西塞进柜子,再次在床上躺了下来。
那个春夜发生的一件事情,才使青梦有了去外地打工的决定。那天深夜,青梦爬到了杨月华的床上,他慢慢靠近她的时候,她突然惊醒了,抓住他的手狠狠地咬了一口。
血从牙印里冒出来,一滴接一滴跌落到地上,叭的一声溅开,变成一枚多刺的栗球,以一种不可逆转的力量,扎向尴尬的沉默。
第二天,他收拾东西去外地打工,临走时他什么都没说,只是对着她憨笑。她明白那笑的内容,她知道那笑的后面,藏着很多东西,有巨浪奔腾,云牵雾绕。她想伸手去挽留他,抱着他对他说:“你别去了,别走。”
她的手像被谁用绳子牢牢地捆绑着,动不了,她张开的嘴,很快又合上,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。她无法告诉青梦,每次面对他时,她都会看到他的背后有一个男人,露出半张冰冷的脸,带着深不可测的目光,向着她走来。那脚步无声无息,不容拒绝地向她逼近,她的每一个毛孔都开始痉挛,那张脸越来越近,倏地进入她的身体,最后消失在并不存在的地方。
她呆呆地站着,远处传来汽车的轰鸣和人群的喧闹,阳光把半边巷子照亮,另一半仍笼罩在潮湿的阴暗里。她看着他低着头,拖着残缺的影子慢慢向前走去,穿过五彩光幼儿园和教堂那扇黑得发亮的沉重的木门。
这时候,晨祷的钟声响了,钻出鱼鳞似的灰色瓦片的缝隙,当当地敲打着浮云低垂的天空。
谁家屋顶的三只鸽子惊飞起来,呼扇着翅膀,绕了一圈后,影子也看不见了。
晚饭过后,儿子对杨月华说:“妈,我陪你出去散下步吧。”
她瞥了儿子一眼,继续拾掇着碗筷。“天这么冷,算了吧。”
儿子识趣地说:“那好吧,我去看会儿书。”
她拿着一个盘子在水龙头下冲洗,水花从盘子里飞起来,溅得到处都是,如同溅在她的心里。
她想过很多,去河边走走,看看夜景,去超市逛逛,去最繁华的奎东路买爱吃的青团。这些念头停顿了一下,很快又像粉牌上的字,在她脑子里抹去了。最后,她决定去附近打一份工。
有次谭红邀她去万家乐超市打工,那是一家新开的超市,有好几个工种可以选择,在槐西路,坐一路车可以直达,比她原先去麻纺厂上班近多了,麻纺厂在筻口,骑自行车紧赶慢赶,都得半个小时。谭红是她的小学同学,一起长大的,她偶尔会上她家里坐坐。谭红那家杂货店关门后,正想找个事做,她们约好第二天去面试。
那天,谭红来了后,等到出门时,她突然觉得浑身不自在,又说不清哪里不对劲。
她满怀歉疚地对谭红说:“你去吧,看来我是去不了了。”
谭红望了她一眼,欲言又止。她感到那眼神有委屈和无奈,还有面对末世般的迷茫。
这几年,她觉得看什么都不对劲,都对着她虎视眈眈。她唯一熟悉的就是从家里去菜市场那条路,那是她唯一的一条路,她一直在苦苦地守着这最后一条路,像一个守财奴守着今生最后一块金子。她心里已经装不下别的东西了,一间柴房,黑暗的角落,勒得人生痛的绳子,两个男人,一个跛脚,一个只剩一只眼睛。这些,构成了她黑暗的世界。
还有一条狗。想起那条狗,她的心里泛起一丝感伤和柔情,那是黑暗里仅有的光明。
她洗完碗筷,给女儿打了个电话,问她什么时候回来。女儿说公司年底忙,要晚一点,恐怕得等到大年前几天。她没再说什么,挂了电话。在这个家里,她最乐意的,就是和女儿待在一起。
女儿回来那天,正好是小年,吃过晚饭,女儿说:“妈,陪我去走走吧。”
杨月华顿了顿,望了眼屋子四周,搓着手说:“那—好吧。”
这是她这几年来第一次答应女儿的这个要求。
她换了身衣服,梳了头发,夹了个蓝色缀白水晶的发夹,戴上口罩,抱着白菜跟女儿出了门。
向左拐出巷子,穿过卖渔具的铺子和对面的小超市,到了临江轩茶楼的门口,茶楼大门两边的走廊上亮起了红红的灯笼,陆续有人推门而入。母女俩并排穿过马路,沿着河边的桂花树往下走。远处的灯一排排亮了起来,脆弱的光从灯柱里溢出,轮番变换着颜色,把冰凉的夜搅得缭乱不堪。栏杆外面,流着一条充满暗示的河流,它沉默,鲁莽而草率,抛开岸边三三两两缩着脖子的行人,我行我素地流向夜晚的深谷。
她俩没有说话,走过这条充满夜色和远方寒风的河岸,从李家码头拐进了县城最热闹的奎东路。自从回来以后,杨月华再也没有来过这里,以前熟悉的一切已经找不到痕迹。她看到行人和车辆像幕布上的皮影,带着慌乱和狡黠从眼前晃过。很多人涌了上来,在老远的地方对着她哂笑、怒吼、吐唾沫。偶尔过来一张帽檐压低的脸,被阴郁的笑容撕裂,他张口想说什么,话未出口就陷入了缄默。他的一只脚还未收拢,另一只脚就匆匆踏进了下一片陌生的黑暗之中。
她停下脚步,环顾了一下四周,灯光影影绰绰,时间宁静而凄凉,她突然觉得呼吸困难,喉咙里像哽着一样坚硬的东西。她感到周围那形形色色的脸正对着她,充满了黑暗的热情,那后面隐藏的邪恶的种子正在发芽,即将长成空心的野草或是灰色多毛的罂粟。
她腾出一只手,不动声色地插进了衣兜里。
女儿见她站着不动,伸手去挽她的手臂。她被这只突然伸过来的手吓了一跳,插在衣兜里的手猛地一抖,一把剪刀当的一声掉在地上。
“妈,是我呢。”女儿笑着对她说。
“哦,我知道是你呢。”她弯腰捡起地上的剪刀,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,“看我记性真不行了,总是忘这忘那,把剪刀都揣到兜里了。”
女儿没有回话,心里的线头像被谁猛地扯了一下,痛得眼泪差点掉了下来。她抹了下眼睛,挽着母亲的手,发现她的手在不停地颤抖。
“回去吧,妈,天太冷了。”女儿笑着说。
“我难得,陪你走走,要不,再走一段吧。”完整的话被她断成了好几截。
“走了一段了,我的脚有些痛了,我们回去吧。”女儿催着她往回走。
她侧过头看了一眼女儿。“嗯,那,回去吧。”
回到家里,她早早地上了床,把剪刀放在枕头边。他外出打工后,这把剪刀就一直放在那,外出和家里来人时就揣在兜里。她没有一丝睡意,剪刀在灯光的抚摸下,闪着黑暗的光,她隐隐闻到了上面的血腥味。
青梦外出打工后不久的一天傍晚,李典平又一次来到了家里,要是别的男人,她打死也不会开门,李典平是个例外。他隔一段会来一次,她知道他来干什么,她预想到了这一次的情形,和以往差不多,喝一杯茶,说几句话,重申一下往事,然后黯然地离开。
她打开火炉,招呼他坐,给他泡茶,倾尽了一个女人的热情。李典平来一次,她就愿意这样做一次。她对李典平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,要是没有他,她至今还关在那间遥远的柴房里。
那个夜晚,李典平闯进柴房里来的时候,她以为自己在做梦,她将脑袋撞向墙壁,以此来确定自己是不是在梦中。李典平示意她不要出声,用带来的刀麻利地割断她身上的绳索,她胡乱套上衣服,被他拽着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外跑。
夜黑茫茫的,一盏灯火都没有,闷热的风在耳边尖锐地叫着。隐约穿过了一片菜地,越过了几条水渠,又过了一条田埂,似乎有什么东西跟着她,被李典平一脚踢远了。然后顺着一条泥巴路跑了一段,在她累得快要趴下的时候,看到了一辆等候在路边的面包车。
上车后,李典平抹了把脸上的汗,喘着粗气说:“快走。”面包车呼的一声往前奔去。
后来,李典平告诉她,他们快到马路上的时候,有一拨人追来了,呐喊声盖过了一个村子的狗叫声,手电筒的光乱糟糟的,像蛇的芯子一样舔向夜空。他回头瞟了一眼,看到他们手里的刀闪着寒光,若再跑慢一点,她一准被抓了回去,挨一顿毒打,他估计就做了刀下鬼了。她只能相信是真的,她脑子里一片混沌,没有了意识,李典平说什么她都会相信。即使李典平拉着她跳河,她也会跟着他毫不犹豫地往下跳。
他们一刻也不敢停留,一路开着面包车回来了。
她没想到还能回来,她以为自己会死在那间柴房里。
她是决定死在那间柴房里的。那是关进柴房里的第二天,她不知道自己身处哪里。
屋里热得要命,灰蒙蒙的,墙壁黑咕隆咚,像是被烟火熏过,一个漆黑的角落里堆着一堆干枯的树枝,看来是做柴火用的,蚊子密集如雨,在那里飞来绕去,无忧无虑地歌唱。她踮起脚尖趴在那扇狭窄的窗户上往外望,希望能看到一点什么,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结果什么也没发现,只看到外面有几棵张牙舞爪的树,再就是淡青色的山,像千层饼一样,一张一张贴向湿漉漉的天边。
头天是一个跛脚的男人来送饭,那个男人脸色蜡黄,缺了两颗门牙,瘦得像一把干柴。他傻笑着,嘴张了半天,才说出一句含混不清的话,她勉强听出其中两个字是老婆。怎么突然就成了别人的老婆了,她气得把饭菜泼到那个男人的头上,吓得他捂着头哇哇大叫,落荒而逃。
第二天送饭时换了个人,四十出头的样子,头发稀稀拉拉,凸出的脑门下,一只没有眼球的眼眶黑洞洞的,像要从深不见底的地方滴出墨汁来。男人绷着脸,一声不吭,睁着唯一的一只眼睛,先是用一种志在必得的眼光盯着她,几分钟后,目光慢慢挪动,从头部到胸部、腰、屁股,那目光阴冷坚硬,像有几条蜈蚣在她身上蠕动。她坐在草席上,努力控制自己的身体,最后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他脸上掠过一丝随风而逝的笑容,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,像一个猎人征服自己的猎物。他把饭菜放下,像发了疯似的向她扑了过来。她又抓又咬,撕打了一阵后,男人气急败坏,挥起拳头,狠狠地砸在她的太阳穴上,她脑子里轰地响了一声,瞬间像一条被巨浪击中的老船,砰的一声散了架。最后,男人从她身上爬起来,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开了。
她躺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空气仿佛凝固了,四周坟墓一般寂静,只有热烘烘的风,夹着一丝甜味儿从窄小的窗里钻进来,提醒她还活在这幸福人间。
良久,她爬起来,把一个碗砸碎,拿起碎片向手腕割去。她挪了挪身子,靠在墙上,她听到血争先恐后地涌向手腕,然后像列队的候鸟一样扑到地上,那声音清脆而欢快,像她躺在自家的老房子里,在一个慵懒的早晨,听着春天的第一场雨。她笑了,血很快就会流干,她将在这间陌生的柴房里死去,躯壳埋葬在异乡的土地里,她的灵魂会飘过高山和河流,顺着长长的铁轨回到故乡那座小城,和亲人们相聚。而这间囚禁她的丑陋的柴房,若干年后会轰然坍塌,在无人看管的春天,长出生机盎然的花花草草,几个孩子赶着羊群从这里走过,他们在湛蓝的天空下,一边骄傲地挥舞着鞭子,一边唱着快乐的歌谣。
模糊中,她听到一条狗的狂吠,爪子在死命地抓着门。
她不知道怎么去医院的,醒来的时候躺在病床上,伤口已包扎好。房门紧闭,一个胖胖的女医生站在旁边,正对着窗口的光在看体温表。见她醒来,叹了口气,“唉,真是造孽。”
她见女医生面善,央求她给家里发个信息,女医生像没听到一样,转身出门去了。
她刚看到的一丝希望瞬间破灭了,像在一个朝阳初出的早晨,一个跟斗翻进了暴雨如注的深渊。她伸手去撕手上的纱布,这时,女医生闪身进来,把手里的纸和笔塞给她。女医生什么话也没说,几个箭步到了门边,肥大的身子紧紧贴在了门上。
她眼里一热,使劲把泪吞了回去,写字的手一个劲地抖。
回去后,柴房被清理得一干二净,盛饭的碗改成了一个木盆子,她的手和脚被牢牢地绑了起来。有天送饭时,一条狗跟着闯了进来,白色的身子,黑色的脑袋,一只耳朵竖起,另一只耳朵耷拉着。后来她才知道,那只耷拉的耳朵不知被谁砍了一刀,留下了一道罪恶的伤口。
独眼男人离开时,狗不肯走。他抬脚踢过去,狗挨了重重的一脚,呜呜地叫着,瞪着眼睛望着他。
她猜,那天救她的,大概就是这条狗了。
后来,每次独眼男人进来,狗就对着他狂吠。狗叫声招来了独眼男人莫名的愤怒,他总是冷不丁一脚把它踢到角落里。次数多了,见到这个男人,狗就远远地站着,前脚弯曲,弓着身子,保持着一副撕咬的姿势。
她总是用眼神制止它,示意它不要过来,她清楚,一旦扑上来,它最后的结局,就是成为这个男人餐桌上的美食。这时候,这条狗的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,舌头伸得老长,呼吸变得急促,双脚不停地抬起,落下。她从这条狗的目光里,看到了愤怒和无奈。
等到男人离开后,它走过来,轻轻地蹭着她的身子,呜呜地叫着,眼睛里布满了泪水。
她对着这条狗,不知流过多少泪。回来的路上,她不停地责备自己,怎么没有把那条狗带回来?她无法把它带走,它必须永远地留在那里了,她只能请求它的原谅。她在恍惚中好几次看见那条和自己命运相同的狗,失去她以后在四处寻找她,它拖着饥饿和疲惫的身子,漫无目的地走着,茫然四顾,乌黑的瞳孔里流露着无人能懂的忧郁和悲伤。
李典平坐下来,两条腿摊开,抚了下薄而顺溜的头发,白晳的脸上浮着不动声色的笑容,这表情和杨月华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。他是青梦的同事,和青梦的关系不错,不时相互走动。他中途辞职去外面经商,贩过钢材,开过皮件厂,搞过货运,包过工程,似乎没一桩生意赚了钱。不过,不管赚不赚钱,他都不着急,衣服经常穿得一丝不苟,头发跟脚上的皮鞋一样,弄得油光水滑,脸上总是笼着层猜不透的笑容。
那次杨月华和青梦去他家串门,他家就在河对面的山脚,那时还没开发,河对面那一片都属于乡村。他家住一栋独立的土房子,门口有一口池塘,屋坪边有一棵脸盆粗的柿子树,正是夏天,绿得发亮的柿子隐匿在欢乐的叶子后面,热切地期盼着秋天的到来。才走到柿子树下,李典平就迎了出来,嘴里叼着根烟,那惯有的笑容,使他脸上的线条显得亲切而柔和。
杨月华凑到青梦耳边说:“难怪他会辞职。”青梦转过头望着她,目光里充满了疑惑。
她笑起来:“你看他这样子,怎么会和你们那些人在那灰尘扑扑的厂子里混?”
青梦点点头,呵呵地笑。
那次,杨月华差点错把李典平的老婆当成了收破烂的。她没有出来和他们打招呼,只是偶尔找什么东西时从他们眼前经过,迈着细碎的步子,又矮又瘦,脸像用刀削过,被骨头撑得快要破裂的皮上,杂乱地分布着白色的线条,那些线条细如发丝,像在凛冽的霜风里走过了漫长的日子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她都还在怀疑他们是不是一对夫妻。
李典平把一杯茶喝完,放下杯子。“这次,得把那钱结了。”
杨月华知道他是为钱而来。当初确实答应给他六千块钱的报酬,东挪西借付了三千,还欠三千,可是家里实在一下子拿不出这笔钱。
“再等等,钱一定不会少你的。”杨月华说。
“我等了两年了。”李典平望了一眼大门,“我扮成收梅子的商人去那个村子,幸亏我早有准备,弄清了那里产青梅,每年都有人上门收购。村里人对我像防贼一样,反复套我的话,只要一句话不对,我就没法活着回来了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接着说,“如果请警察来解救,这点钱远远不够。不是看在你老公的面子上,这种事打死我也不干。”
“我知道,你说的都是实话,是我们欠你的。”杨月华把头埋到胸前,她从心里感到,确实是欠了人家的。
“好,那今天你无论如何都要把钱给我。”李典平站起身来,向着杨月华慢慢逼近。这时,她闻到了他身上那股浓浓的酒气。
看着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不断靠近,杨月华攥紧了裤兜里的剪刀。李典平把一只手搭到她肩上,她惊叫了一声,操起剪刀刺了过去。她看到李典平猛地睁大了眼睛,像看到了外星人一样,五官随即扭在了一起,好像要从脸上跌落下来。
他龇着牙,一只手死死捂着手腕,呻吟着,夺门而去。
剪刀掉在瓷砖上,当地响了一声。杨月华站着没动,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她压根没有想到,自己会这样做。
腊月二十六的晚上,杨月华躺在床上发呆。
青梦发微信来,厂里事多,今年不回来过年了。
他已经有两年没回家过年了。
平时,他经常会给她发信息,主要是说一些过去的事情,他对过去的事都记得十分清楚。说完一堆事,后面总不忘加一句,慢慢会好起来的。
她总是简单地回一句:“嗯,知道了。”
她也想慢慢好起来,她不知道,这个慢慢是多慢。
她拿着手机摩挲了一阵,在寻思该如何回他的信息。她心不在焉地在屏幕上点击着,结果打出了这样一句话:如果走得开,就回来吧。
她反复看了几遍,点击发送,好像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事情。她觉得有些累了,把手机丢在一边,把白菜揽过来,闭上眼睛,希望尽快睡上一觉。
天亮时分,她又做梦了。
梦见那个独眼的男人,五花大绑,被警察押着跪在一片荒地上,然后枪响了。黑色的血像一根柱子一样从他后脑勺上弹了出来,然后散开,如柳絮般溅落在荒草上。
她被吓醒了。她问自己,这是她想要的吗?她摇了摇头。
她听到外面响起了鞭炮声,沉沉重重,随风涌向窗外,仿佛一股潮水从巷子的另一头漫了过来。还有三天,就过年了。她爬起床来,站到窗前,把窗帘拉开,巷子里空荡荡的,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左手边的高楼上,悬着一盏昏暗的灯,这高楼上最后一盏灯,随着白天的降临,很快也要熄灭了。
她抬起头,看到了屋檐下的天空,灰白的颜色,沉沉地压下来,像压在她的头上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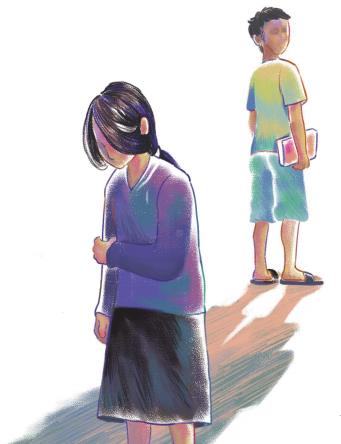


 微信号|长沙文艺
微信号|长沙文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