去崇山峻岭之中的五宝田,并不容易,沿途需经无数险窄的“山路十八弯”与“水路九连环”。或许,正因为不容易,才更坚定了去的信念。
五宝田,是田畴的名字,更是一个村庄的名字,隐匿在辰溪、溆浦、中方三县交界的雪峰山与武陵山大山深处,隶属于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。
五宝田,之前的名字,应该是叫作兀泡田,或者是别的什么名字。兀,是高而上平,高耸突起的意思。后来不知何时被何人改为了五宝田,总之,不管叫什么名儿,都掩盖不了这个大山褶皱里的历史文化名村的光芒。这大概是被寄予厚望的地名,村里自古到今,出过富甲一方的商人,也出过前清的秀才,当世的教授。现在,大概能记住以前名字的只有村里八十多岁的老人了,萧守造老人就是其中之一。萧老今年已是八十七岁高龄,却腰板挺直,精神矍铄,见我们一个个晕头转向下了车,便操着浓重的方言迎了上来,先是寒暄握手,然后用土坷垃似的声音给我们解说,声音带着穿堂风似的混响,从不断歙动的喉结处涌出来,透出一股子自足平和的古拙之气。
古村给人的第一印象,古朴、干净、馨宁,颇有亮眼之感,大概心中想象的世外桃源就该是这个样子。我们从城市一路逶迤而来,绕山绕岭,抖落一身喧浮之气,一脚踏上这片土地,内心竟然有些小激动、小确幸,所见皆是寂静、安闲、葱绿、新鲜。
村寨前坪,散落一大堆竹筒。青绿色的竹筒,被截成一长段一长段的。一位八旬老人,戴了顶塌檐黑色布帽,脚穿黑胶防水套靴,佝偻着身子,一手拿柴刀,一手拿锤子,只见老人把柴刀对准竹筒边缘,用锤子使劲敲打,刀锋嵌入竹筒,继续握着柴刀,往下瞬间发力,架在木板凳上碗口大小的楠竹,一节一节,毕毕剥剥,顺势就劈裂开来。原来,不用锯子,也可以把竹筒劈成想要的大小尺寸。同样的动作,重复,再重复,粗大而青绿的竹子,就这样被老人劈成细小的条条片片,堆叠、打捆、扦插,适合做成菜园的篱笆,既整齐,又美观。竹筒和竹片,一定还适合做一些其他的用途,农村的诸多事情,多神秘而阔大,各种灵巧的篾织活儿,远超人的想象。略略抬眼,不远的油菜地边,虽非采菊东篱的时候,一排排整齐的竹篱笆,倒似在列队迎宾,欢迎我这远道而来的外乡人。
说实在的,寂于深山一隅的古村是否欢迎我,是否需要被外人打扰,我不是很确定。事实上,现在,已经没有多少真正能被人遗忘的乡村了,即便是山高路远,总有被人踏过的脚印,和即将要踏上的脚印。世外桃源,只能是存于每个人心里的梦境。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当乡村游成了网红热门,当村居生活成了大多数城市人的诗和远方,一切都需要被重新定义。从一开始的乡村人逃离乡村,到现在的都市人纷纷走进乡村,乡村人渐渐回归乡村,当下的乡村,就该有新的觉醒,新的认识,或者说是早已经觉醒了。
连通山外世界的,是一条简易的水泥路。
山路弯弯,重重叠叠,所幸有这样一条还算体面的水泥路。我无法想象先人们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,又是如何肩挑背扛,开采当地特有的玉竹石,把这一幢幢房屋建得如此古雅、精美。水泥路并不宽,曲曲折折,或许好久没有人养护,两边长满了茅草,这似乎有些让人意外,但我转念一想,这大概是人们刻意留着的吧,显出本来的原生态。谁又知道呢?“原生态”这个词,如今已经被人们用得太过泛滥,但真正的“原生态”,却是多么可遇而不可求,让人心生向往。
村口视野开阔,连接溪水两岸村寨的是一座拱形石桥,桥尚新,大概没修几年,也很宽,可通车,可行人。村人往来,即使扛着锄头,背着背篓,戴着斗笠,皆有闲庭信步的感觉。桥上,一中年男子牵着红衣小女孩从桥头走来,手上拿着花花绿绿的塑料玩具。他们用好奇的眼神打量我们这一群外乡来的不速之客,眼神里分明有着一些从容与自豪。山外有的,他们现在大抵也都有了,可山外,却无法拥有他们这里亘古不变的青绿山水。他们过着平静的日子,神态自然而大方,本乡本土人的闲适,倒是一种别样的风景。相反,站在桥头迟迟不前的我,似乎有着某些犹豫,或者说有些焦虑,羡慕是理所当然的,同时又有些小感伤。我成了他们眼里的外乡人,虽然我的家乡,在不远的隔壁邻县,但我却空有满腹乡愁,更多时,成了回不了家的孩子。
村子前坪,一个简易棚子里,摆一架加工棉花的机子,旁边是一堆生活用具,与古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是什么人住在这样的棚里?我正纳闷着,眼见一个年轻妇人坐在水泥台上,一勺一勺地,很是耐心地给孩子喂米糊,孩子张着小嘴,甜稠的米糊很养人,很快就吃了个碗底朝天,几个月大的孩子看起来有岁把左右,现在的孩子都长得飞快。一打听,原来,这也是一家外乡人,从河南而来,是暂居村里的棉花加工作坊的主人。我走上去和妇人攀谈,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,当地的老人孩子都听得懂,也乐意听她聊山外的事情。一开始她听不懂本地话,后来渐渐能听懂一些,沟通自然没有问题。年轻的男主人在一边和村里一位戴斗笠的大妈交谈着,只见大妈笑盈盈地掏出一百元递给了男子,并道谢,然后背着看起来很厚实的新棉被回家。大妈只需绕过几丘水田,就能回到溪水边那栋有白色风火墙的木屋里。高低错落的水田尚未插上秧,蓄满了田水,如镜子一样,映着大妈粉红的被面,给古朴的村寨添了一抹云霞似的亮色,当然也倒映着绵延的山,映着天空中即将散开的云层,整个画面生动、活泼、立体。问起他们来村里多久了,男主人似乎也很健谈,说是在这里住了快一个月,等把村里的棉被都加工完就该要搬走了。他们这两年来拖家带口,一个县又一个县地奔走,一个村又一个村地驻扎,一家又一家地上门服务。大山深处的村落里,棉被加工似乎不太方便,特别是老人家居多的乡村。别看现在生活条件好了,家家户户电器都摆满了角落。可是,很多老年人很节俭,一辈子舍不得换几床新棉被。以前的老棉被舍不得换掉,又旧又硬。
现在,棉花加工的人上门来了,老人也图方便,把旧棉絮重新弹一次,或是添上新棉花,弹一床扎实的新棉被,盖着软和温暖,再冷的冬天也不怕了。男主人说着说着,似乎有点自豪起来,说忙碌的时候,一天要加工几十床棉被。只是,最近,来找他们加工的越来越少,除了雨季的原因,估计是家家户户都更换得差不多了,看来,得赶去下一个村子。人们都暖和了,他们离搬家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
石桥下,一弯玉带般的溪水绕行,舒缓而自然,把古村环绕其中。溪水丰盈处,拦成水坝,泻出一排好看的瀑布,村里整日流水哗啦哗啦,水,或动或静,静影则成碧,飞花则溅玉,水上白鹭时飞时停,水下游鱼往来嬉戏,水草青荇,如丝如绦,皆各有风姿。偶尔传来婴儿的哭闹,黄狗的吠叫,夜里自然还有蛙鸣,寂静掩柴扉,苍茫对落晖,一个村子该有的模样,热闹的、安静的、古朴的、烟火的,就都具备了,真正是一幅“清风入弦,虚徐其韵”的田园村居图了。
进到村落,一切都是那么亲切。村屋飞檐翘角,次第排开。只见墙头屋檐层层叠叠,鳞次栉比,顺着山的走势而上,背靠高山龙脉,左青龙,右白虎,看起来风水极佳的样子。难怪三百多年前的兰陵萧姓祖先要选中这块宝地,作为他们家族繁衍生息的根基所在。这些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深宅大院,都经历了一些什么?为什么看起来,除了风雨侵蚀外,依然是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?所幸的是,这座古村落依然活着,一代又一代,生生不息,烟火漫漶。
我,突然有些内敛地小心翼翼起来,为自己是家乡走失的一名游子,只能在别人的村子里晃来晃去而心存怯意。青砖、白墙、小青瓦、檐角、门梁、照面、廊坊……从诸多老旧和破败的事物中,依然能看出前朝的规模和气象、大户人家的智慧和匠心、百姓人家的仁孝和谐,能看出这里一直秉承“耕读兴家”的祖训。斑驳脱落的白墙依稀可见红色标语,从模糊不清的彩绘门梁,从颓垣断壁的老土墙,从长满青苔的石板,从雕花的木窗户,从嘎吱响的木门,从锈迹斑斑的铁皮门,依稀可见当年那些烟火漫卷的画面。家家户户的木门里,又裹了一层结实的铁皮,据说是为了防火灾和土匪。屋外有风火墙和闸子门,屋内有几家人共用的屋檐和天井,有着近乎完美的排水设施,雨天屋里不潮湿,人在院子里走路不湿鞋。沿着青石板小路,在村里绕行一圈,我突然有时空错乱的感觉,要不是下着蒙蒙细雨,真想找个安静的屋檐下,面对脚下流淌的一河溪水,坐一坐,想一想,面对一些流去的旧时光,乡村该如何回顾历史,该如何传承与发展。
风雨桥上,又遇一位萧姓老人,八十六岁,正眯着眼看向远方,拐杖靠着桥栏杆,他坐在桥中的木凳上,听着桥下的流水,数着自己一圈又一圈的年轮,似在回忆老旧的故事。只是再也没有人听他的唠叨,再也没有人知道他年轻时的模样。他的孩子们都去了城市,要待到每年十月庆祝“盘王节”才会回家,他们大部分是瑶族,还依稀保留着这个民族一些特有的风俗。老人娓娓而谈,他把自己的故事,告诉我这样一个在村里逛来逛去的外乡人,或许是需要倾听者,或许是说给风听的。他说话的时候,已经看不出脸上悲戚的表情,实际上,他已经老得没有多少表情了。
溪水边的振青园,古朴典雅,能看见颇完整的门楼,世间风雨的侵袭,依然没有放过这个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老宅子。坐在振青园门口的萧守造老人,却越老越精神,依然受人尊敬,他老成了村里的金牌导游,也活成了人们眼里的乡贤。他面对祖先留下的这幢房子,解释说,之所以叫振青园,是寓意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,告诫子孙后代要耕读传家,承先人之学,光耀门楣。
乡风文明,是一个村庄的脸面。五宝田能有好的风气教养和礼仪传承,得益于村口的耕读所。建于1893年的耕读所,是村里最有灵魂的建筑,是村民储粮和耕作之余拜读诗书礼仪的场所。耕读所是一处独特的井院式建筑,正楼五开间,屋顶为歇山顶,屋角轻盈上翘,两翼横屋则采用悬山屋顶。萧氏祖先择居此地之后,一面勤劳持家,一面训育后代,要求子孙后代不仅要勤俭持家,还要勤奋学习,用智慧致富。大门横梁上用青花细瓷所嵌“三余余三”四字,苍劲有力,耐人寻味,寓“耕读兴家”之意。三余,即“冬者岁之余,夜者日之余,雨者晴之余”,意思是提醒读书人要珍惜光阴,倍加努力,学足三余。余三,即“三年之耕而余一年之食,九年之耕而余三年之食”,意思是教育后人要勤俭持家,居安思危,时备饥荒。
耕读所大门对联“一水护田将绿逸,两山排闼送青来”,由于年代久远,字迹斑驳,依稀可见。一楼为乡贤讲堂,二楼有宝凤楼。乡贤讲堂里桌椅板凳齐全,定期还有先生来讲课。宝凤楼因形似凤凰而得名,旨在筑巢引凤,吉祥如意。宝凤楼圆门上方左右两侧分别题有“教”“养”二字,“教”是教书育人,“养”为丰衣足食之意。宝凤楼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,三百年来一直秉承儒家理念,遵循孔孟之道,成为镶嵌在村里巍巍群山中的一颗耀眼明珠,也是村里人最重要的精神家园。二楼书屋摆放着一排排整整齐齐的书架,书架上有各种线装书,如《传家宝全集》《处世绝学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元曲名篇鉴赏》《水浒传》等等,还有用于休憩、品茶、论道、交友的休闲区,体现了人格的平等,营造了浓浓的人文气氛。一楼还有烤火房、仓屋、马厩等,也都体现了建造者的匠心和人文关怀。从耕读所雕花的窗户往外看去,一座宁静的村子静静地伫立在玉带溪对岸。三百多年来,在这里读书的孩子,不断地走出了村落,走到了人世间,在翻阅了人生这本大书之后,又会纷纷回归。他们一切知识的启蒙均源于此。先人教育他们重孝道,知感恩,传美德;教育他们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;希望每一个村里少年都能“束发为髻,化蛹成蝶”。
溪水边,田地里,油菜已经饱满成熟,有的已经匍匐在地,要赶紧收割了。枇杷树上缀满黄灿灿的枇杷。五月是美丽的,五月也是忙碌的。放水、犁田,好赶上小满之后的插秧。只见一家三口在田里忙着,他们用镰刀把泛黄的油菜收割,一抱一抱,铺在地上,只待出几个日头,油菜荚晒干,铺一床竹篾垫子,用一根长长的棒槌,啪啪一顿拍打,菜籽四处蹦出,清理掉细碎的荚壳,用箩筐挑回家,再晒几个大太阳,或是用火焙干,用古法榨油,能收获满缸香喷喷的菜油呢。三五丘田,都收割下来,一家人一年的菜油就足够了。
劳作是快乐的,也是美好的图景。收割油菜的一家人,似乎并没有发现我这个外乡人在偷拍他们,或许早就发现了,但这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影响呢,他们仍然埋头干活,和日子赛跑,创造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。我想,除了建筑之美,劳作者的身影,也是这个村里一道最美的风景吧。一位大叔模样的乡亲,用推车拉来一车沙石,他想把自家的坪场也打上水泥地面,这样,过节的时候,从城里回来的孙子,就有放鞭炮和嬉闹玩耍的地方了。另一位头发泛白的大叔,坐在风雨桥上歇息,或许是干活累了,或许是因为下起了小雨。他掏出手机,乐滋滋地玩起来,不时被手机短视频的搞笑逗乐。
置身美丽乡村,穿行在久远的历史中,烟雨迷蒙,似乎眼睛和大脑都不应该放空,还真应该想点什么,感悟点什么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每个乡村也是独一无二的,有逐渐振兴的乡村,也有渐渐消亡的乡村,每一个乡村自有它的气象和命运,人生也各有不同。人都有来处,也有归途,人生处处都是起点,不必太过纠结未来是什么样子,我们谁也不清楚,只求耕耘,不问收获。但愿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,都能珍惜当下,与自己和解,顺应时代,努力追寻,各自安好,便是晴天。这样想着的时候,我是不是一个外乡人,是不是能找到回乡的路径,似乎已经不太重要,也似乎有了一些答案。
临走的时候,同行的才子海文社长录下一首《临江仙》,一手漂亮的粉笔字,留在溪边的一块大青石板上。或许,看着流淌的溪水,容易让人内心生出诸多感慨。如川之逝,不舍昼夜。三百多年前的萧氏祖先,如今何在?浪花淘尽英雄,是非成败转头空,青山依旧在,夕阳几度红。
细雨,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,时间却不等人。我这个外乡人,除了悄悄地来,也该悄悄地走了。我能带走什么呢,我得把热爱和欢喜带走,留下一脉青山、一溪绿水的回忆。是的,不管我来与不来,一些藏在大山里的小美好,正井然有序地发生着,我用眼睛所看到的,用心灵所感受到的,总是那么蓬勃、葳蕤,并不似从前的斑驳和古旧。我只是希望,我没有打扰到这里的宁静、祥和、与世无争。
我想起聂鲁达的一句诗:“我要在你身上去做,春天在樱桃树上做的事情。”但春天远了,樱桃也落了。一个路过的外乡人,终究是要回家的,回归自己的来处,包括那对河南的小夫妻,包括曾经迷失在城市里的萧氏后人们,还有那些来过村里的行者,以及将要归来的后来人。
回望车窗的时刻,我微微仰着头,山岚雾色里,默默期待,每个人的家乡,都美好如初,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,都可以站在原地,向着故乡伸出双手,一只许以温情,一只给予抚慰,与子同衣,生死不吝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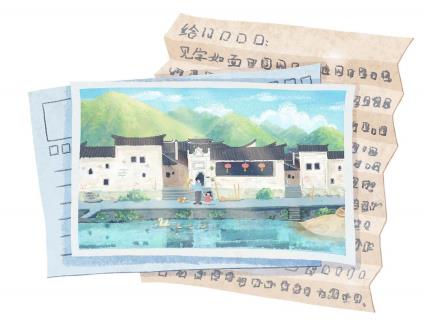
 微信号|长沙文艺
微信号|长沙文艺